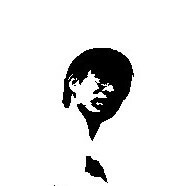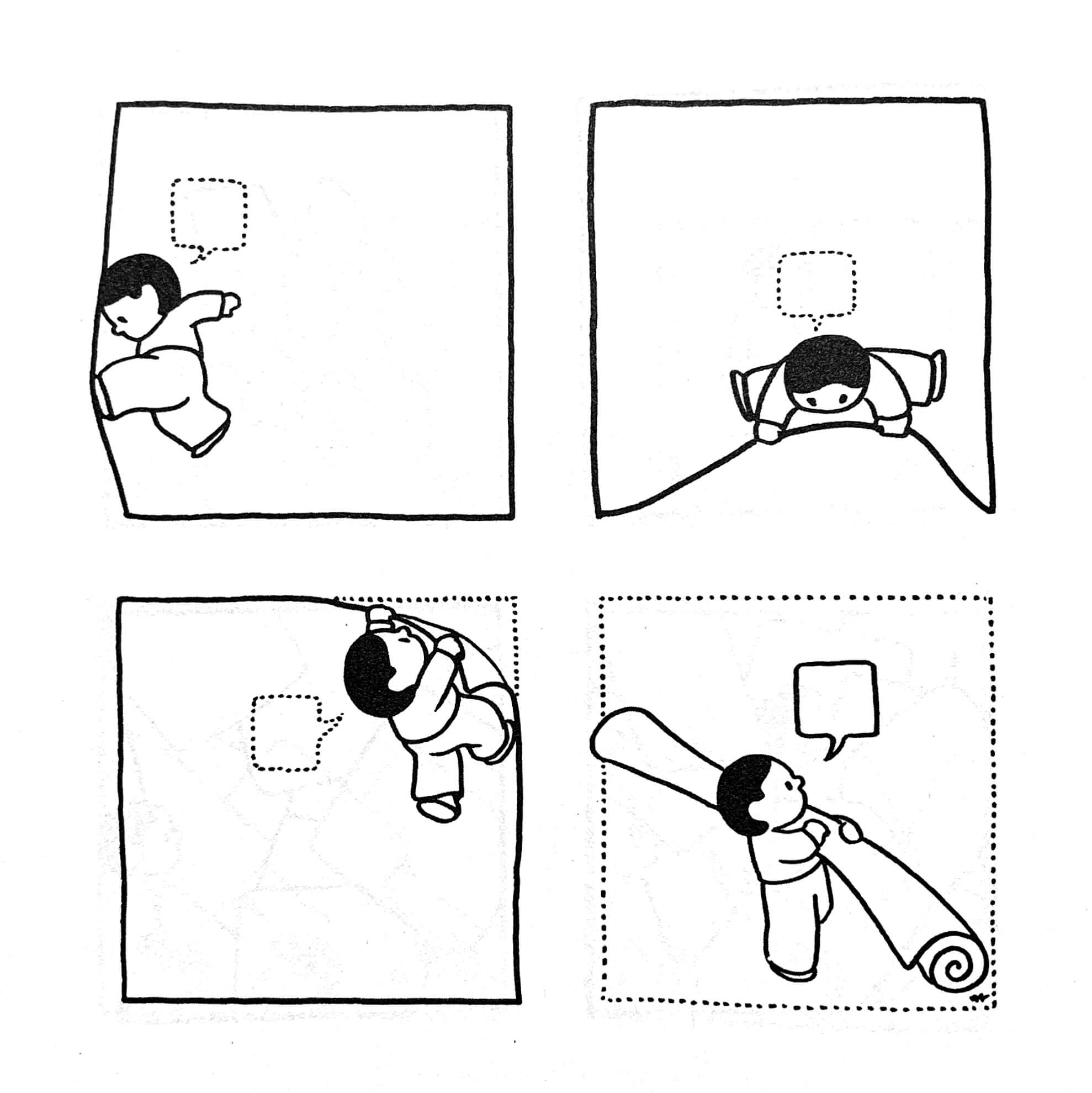8 8 月, 2014 § 乡土,似曾相识却未曾相识 —— 重读《乡土中国》已关闭评论 § permalink
家乡有她的一种魅力,这种魅力被人们概括为「乡土」,乡土是一个漂亮的词。然而,家乡让人思念,却再也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乡土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以读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是费老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学期间所写的讲稿,并连载于当时的《世纪评论》。按费老先生自述,书中诸多概念,甚至「乡村社会」这一议题本身其实都是费老一边讲学一边探索出来的,在当时学界还属空白领域。多年后,重读此书,费老先生为他年轻时代的那股闯劲所触动,而我们则庆幸能一睹老一辈学人的卓识与风姿。书中,费老多处强调里面很多概念是不成熟的,即便如此,当中诸多令人赞叹的洞见及深入浅出的社会学分析对当下仍有积极意义。无可否认的是,乡土社会已渐渐远去,但乡土观念却依然主导着我们的生活。
回到文本。费老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源于先人所坚守的一种「无需流动」的生产方式(农业谋生)和生活方式(聚村而居)。因之,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人都是别人看着长大的,这造就了一种天然的默契。基于这种默契,乡土社会形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社会形态,它的「土」、「愚」、「私」、「法」、「礼俗」等等都有着鲜明的内在逻辑。对此,费老在书中做了非常有趣的分析,本文不作赘述。我愿意列举几段印象深刻的文字,与大家一起思考。
1、
书中,费老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说的是: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西方)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越远,也愈推愈薄。(P34 ①)
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能伸能缩的能力,这造成了群己、人我的界限划分非常模糊,因而公和私是相对的。由此,费老引出一个很有趣,却值得深思的推论: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 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P38)
细究一番,中国人可不正是这样。很团结?似乎不是。很自私?好像没有。我们只能用很中国的方式来作答:这个很难讲/看你怎么讲/随便你怎么讲。然而,如今我们已不能这般马虎地回应这一问题了。我们不得不反思自古以来的道德教育,为何它慷慨激词,却收效甚微。它太虚伪了。茅于轼在《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中分析了道德的悖论,儒家的君子道德想象其实是不成立的。而费孝通借「差序格局」对「私」的分析,让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集体主义道德教育的无力与虚伪。可是,我们终究是需要社会道德的。在差序格局里,社会道德如何重建?差序格局中的人是否注定就是「私」的?如果是,这近乎人之常情的差序格局,改良还是解构?费老先生没有给出答案,但我们需要解答。
2、
在第6章,费老先生谈到了「家族」,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在结构原则上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P57)这与西方家庭非常不一样。具体是: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情感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P57)
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角 …… (乡土社会里)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什么话可说的」。(P57)
考察现代中国家庭,不难发现,其主轴仍是父子与婆媳。《新周刊》如此评述现代爱情:「我们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物质基础,这么自由的两性关系,但我们创造并迎来的,却是史无前例的,岌岌可危的爱情时代。」② 原因在于,浪漫的人们在选择婚姻之后,便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陷入这种传统的以父子/婆媳为主轴的,纵向的差序格局之中,夫妻变成了配角。如今,多少夫妇还是把子女当做他们一生最大的依靠。而遗憾的是,这却是最失败的赌注,因为他们开始彼此疏远,继而失去了「爱」。我尤其想指出的是,「爱」的缺失将导致「家」的缺失,而没有「家」的老夫老妻其实也是剩男剩女。所以,我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实际上是不饱满的,它不能文化地存在,而这意味着「家」尚未完成,一个未完成的「家」并不具备幸福的条件。
这里,我愿意分享我对「家」和「爱」的期许:一如艺术凭藉人的创造力将我们的情感塑造成现实,我们通过对「家」的创作将「爱」塑造成可感的现实。而这需要我们将「夫妻」调整为差序格局中的主轴,并还子女以自由。
3、
费老先生在书中对「礼治秩序」和「教化权力」有多处论述,以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人们)一代一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路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P71~72)
凡是比自己年长的,他必定先发生过我现在才发生的问题,他也就可以是我的师了。三人行,必有可以教给我怎样去应付问题的人。而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出则悌。逢着年长的人都得恭敬,顺服于这种权力。(P97)
如今,这种教化权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而不同的是,旧经验已经无法因应新生活了。然而,父辈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与乡土社会已然大不相同,或许他们也不愿意放弃这种教化权力。中国父母对子女有着太强的占有欲,总想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子女。也许他们意识到观念的差异将造成难以逾越的代沟,这将肢解他们固执的以父子/婆媳为主轴的家庭观念。在普遍把代沟问题归咎于年轻人的今天,我必须善意提醒,与向传统看齐的乡土社会不同的是,现代社会以「未来」为标准,如果父母不「学习」,恐难以与子女共享未来。
此外,这种对传统教化的顺服使得我们没有成长的机会。林奕华认为中国的文化和传统是一直在打压成长的,我们的文化要求我们只需成熟。③ 因为我们在出生之前,前人已为我们备下答案和标准。于是我们只需知道答案,而无需问问题,无需去尝试。我们不能试错,因为我们不能犯错。在传统观念里,所谓成熟是指,当你的想法和行为和大人想的一模一样的时候,你就成熟了。可是,这种成熟是荒诞的。当我们盲从传统,只求答案,而对事物失去陌生感,失去求索的热情,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反思」的能力。当我们失去成长的机会,不能亲身体验一个「过程」,我们就失去了「感受」的能力。然而,当一个人既不能「感受」又不能「反思」的时候,你还能指望他拥有什么的人生?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分享更多的想法。我特意挑选这几段是因为它们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是我们必须予以回应的社会/生活难题。此外,这几段所讨论的都是「乡土」观念的消极影响。关于「乡土」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仅仅限于一种美好印象,似曾相识却未曾相识,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更现实的一面。在拥抱城市却发现得不到城市的温暖的时候,人们往往对乡土投以新的期待,而得到的却可能是更残酷的打击。我想说,这种对未来的城/乡二元想象其实是方法论上的错误。
诚如费老先生所言,「在我们社会的极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P9)时下的道德困境、城乡困局等莫不与此相关。在谈及城市与乡土,现代与传统的时候,人们常常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简单概之。事实上,当我们真正深入考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乡土」的悖论性感到困苦。有个值得思考的例子,一方面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是「私人定制」的,具体的,雷吉斯•德布雷更是将这种友谊视为奇异的经验,在个别之中取得普遍,无虚伪也无空话。④ 然而,传统的诸多规训却让这种友谊变得愚钝、虚伪。赵汀阳提醒人们,现代概念每天都在规训着我们,体制化地塑造着我们的感受方式。⑤ 而我想说,传统礼俗同样如此。乡土社会已渐渐远去,乡土观念依然主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仍须面对「乡土」这一悖论性存在,我们须对它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我想,我们应该感谢费老先生的工作。
注:
① 文中所有的页码标注都是北京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相应的页码。
② 《新周刊》2006年第3期:保卫爱情。
③ 林奕华:艺术终究是个人成长。文汇报,2014年5月2日 副刊 A26
④ 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2014,p097
⑤ 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两面之词,2014,p036
……………………………………………………
本文遵循CC知识共享协议(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演绎)。
这篇文章是应广州湾青年会馆之邀为第一期「壹书壹会」而作。
2 11 月, 2012 § 请不要把我埋葬在“新闻联播”里 —— 重温《楚门的世界》已关闭评论 § permalink
“早上好,顺便预祝午安和晚安。”每天,楚门都这样以他标志性的笑容开始崭新的一天,他开朗、乐观、幸福,但他不知道,十七亿观众正注视着他,他其实是位“演员”。某天,楚门偶遇离世多年的父亲,由此产生疑惑,他想起他的初恋 —— 罗兰,想起罗兰所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语。之后,虚设的电梯、飞往斐济的飞机、突然故障的火车、“走不远”的道路、摩可可饮料、死而复生的父亲…… 楚门愈加感觉到,他生活在一场“阴谋”里。
这时,摆在楚门面前的是一个残酷的问题:离开,还是留下?离开,他将面临一个全然不同的环境,他会失去与他生活几十年的朋友,甚至一切的一切;但若留下,则意味着他将继续生活在“虚假”之中。
我们的直觉排斥虚假,但问题是,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在楚门逃离剧场之时,制片人克里斯托(Christof)这样劝告:“外面的世界比我虚构的世界更不真实,同样的谎言、虚伪,但在我的世界,你不必害怕。”无独有偶,影片《牛津杀手》也有一段类似的对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赝品收集地 … 在这里,我觉得很轻松,没有人欺骗我,实际上,这是世界上包含真相最多的地方,我们有一个绝对真理,所有事物都是假的,在这些墙的外面,没有人会对任何事情有把握。”
克里斯托所言非虚,“离开”就远离了虚假?不尽然。反过来,“留下”就真的意味着虚假?很难说。
有个关于机器人是否具有人类智能的测试,亦即图灵测试(Turing Test)①,说的是,测试者(人)在与被测试者(机器)隔离的情况下,通过一些装置向被测者随意提问,如果测试者不能判断是人在回答,还是机器在回答,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认为具有人类智能。藉此思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类似的测试(不妨称之为:楚门测试,Truman Test):一个人(测试者),一个生活场景(被测试者),如果这个人在此场景生活足够长的时间后,无法辨认这是真实生活还是虚构的一场戏,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一生活场景是真实的。
在这一意义上,《楚门秀》就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克里斯托解释说:“楚门虽然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但他自己本身却半点不假,没有脚本或提词卡,这是生活实录。”楚门的爱妻,梅莉(Meryl)说道:“我的生活没有分所谓的私底下或是电视上,《楚门秀》就是我的人生,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而且非常幸福。”楚门的朋友,马龙(Marion)同样持此观点:“全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这场秀绝对不假,只是经过设计。”
《楚门秀》不同于其他影剧,没有人告诉楚门要表演什么,如何表演。在剧中,楚门可以自由言说,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不离开海景镇),就像正常人一样。最要命的是,这虽是一场戏,一个虚构的生活,但它同样能提供人们最为渴望的东西,幸福!这里有爱情,有亲情,有友谊,有事业,有梦想,有挑战,有偶然性 …… 甚至还有性。所有的这些都使得《楚门秀》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真与假的界限,如果没有那次特别的意外,楚门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然而,无论机器程序如何聪明地狡猾地欺骗了人类,在本体论意义上,机器终究还是机器。同样的,无论虚构的生活如何逼真、生动,虚构的生活终究无法与真实生活相比拟。我们能隐约感觉到,在虚构的生活中,即便能得到同样的生活体验,剧中的“我”和真实的“我”其实并不同一。病了的苏格拉底和康复了的苏格拉底毕竟很不一样。②
文艺复兴以后,人们的目光逐渐由神性转向人性,心灵全面开放,人开始成为精神主体。特别地,牛顿的革命让人们越来越相信人类其实是可以驾驭自然的,而且“不需要上帝”③,而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④更是让主体性(subjectivity)深入人心,人们相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自己是自己精神的权威,“人是万物的尺度”,甚至干脆说,“我”就是尺度。如今,这些观念不仅已经普遍化,而且非常自然地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实,古往今来,人们至始至终都在关注着自我(ego),如周濂所言:“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我是谁”,这是一个俗到无以复加的问题,在历史上已被人们无数次讨论,然而,事实上,这类问题及其讨论至今仍在重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无可回避,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及其答案之中。薛定谔甚至认为“我是谁”是人类所有精神追求的真正源泉。我很感兴趣楚门会怎样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楚门知道自己的境遇后,楚门会怎样看待“楚门”,楚门还会坚定地说“楚门就是我,我就是楚门”吗?
虚构的生活削弱了自我,同时剥夺了生活的意义。虽然楚门一直都很自由,但他毕竟在剧组的控制之下,剧组可以轻而易举地影响楚门的生活,例如,剧组曾无情地夺走他所深爱着的父亲和初恋情人。在一个受控制的生活里,自由和幸福其实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经典机械论对伦理及生活意义产生的冲击。如果拉普拉斯所言为真,世界是决定论(determinism)的,那么,自由、意志、理性、价值等将荡然无存。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人们不再有欲望,不再喜怒哀乐;人们将生无所求,死无所惧;人们对未来没有期许,因为无从期许;人们不再思维,因为无从思维。这样,生活就没意思了,生活意义被消解,而其后果恐怕是灾难性的,不难理解为何无数哲人这般殚精竭虑,极其不安地修补着机械论世界观,“生活死了”比“上帝死了”要糟糕得多。克里斯托给楚门许诺一个“不必害怕”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处境会好于楚门吗?
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能自信地回答“我是谁”,并“是我所是”地生活么?
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能“自由”地开拓生活意义吗?
我们的世界或许是真实的,但我们却没有理由感到乐观。我愿意再次重复克里斯托的所言:“外面的世界比我虚构的世界更不真实,同样的谎言、虚伪……”地沟油、有毒牛奶、豆腐渣工程、腐败、贿选、新闻失真、司法黑幕、作秀 …… 所有的这些都深深地打击着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信任,我们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红十字会,不相信爱情,甚至连不慎跌倒的老人都不敢信任。我们的世界是真实的,但我们彼此却不信任,深深地不信任,而一个彼此不信任的世界会是“真实”的么?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世界里,或许没有超越性的他者控制着我们,但我们却受制于自己,我们受制于自己的欲望,受制于自己所创造的种种观念,我们将自己深深地束缚在所谓的“现代性”(modernity)之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功利主义、科学主义、机械主义、消费主义…… 人们制造观念的本领丝毫不弱于上帝,然而,如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那样,这些观念不幸使得人们的思维片面化与教条化,同时导致人们世界观的破碎,以及人文思想的衰落和生态文化的失衡。
在寻常生活中,常人并不容易觉察到这些观念对自己的“欺骗”,原因在于,当我们相信这些观念,我们就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其他观念,这样,自己所坚信的观念显然总是正确的,而“异己”则总是错误,于是,我们一直固执己见(哪怕它荒诞无比),此时,我们就已然被“观念”控制了。事实上,没有一种观念在理性上是可以自明(self-evident)的,哲学对自相关(self-reference)的论辩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任何观念都有其固有的局限。可惜的是,人们往往不清楚也不在乎观念的限度,特别地,在很多时候,人们接受某种观念并不是基于理性思考,而仅仅是因为“别人也这么认为”。这种对观念的盲从使得大众非常容易陷于观念迷局之中。哲学家飞不出蝇瓶⑤,普罗大众更加逃离不了观念的牢笼。
笛卡尔认为不可怀疑的我思(cogito)证明了主体的绝对自由,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我思”的确是自由的,但“我思”的产物却不知不觉中束缚了“我思”及“我之存在”。人们自作聪明地在观念世界中寻找自我,却反而让自我迷失在观念世界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与此类似的还有时尚。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在关切着自我,都有着一定程度的表达自我的冲动,都希望通过个性以强化自我的存在感,时尚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关于时尚的分析,西美尔有段深刻的洞见:“时尚的本质是分界和模仿,是普通大众向更高的阶层显露自己一种方式”,“时尚对于那些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凭借自身努力达到个性化的人而言是一种补偿,因为时尚使得他们能够加入有特色的群体并且仅仅凭着时尚而在公众意识中获得关注。”(参见[6])普通大众通过模仿时尚而加入有特色的群体,使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了分界,这种分界让人们至少在心理上觉得自己有个性。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时尚貌似表达个性,却是最没有个性的表达方式,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模仿。时尚的这种悖论性不仅无法成就自我,反而使自我变得面目不清,让那个最纯真的“自我”消失殆尽。
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察。这是一个万物皆商的年代,赵汀阳指出,“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无限商业策划的时代,这暗含着一个从征服物质到征服心灵的基本转向”,商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的途径之一是大批量生产并无限扩大销售,无限扩大销售就必须吸引大量顾客,而实际上,人们并不需要购买那么多的商品,这样,商业就必须设法说服尽可能多的人相信那些生活上不太需要的东西其实是生活所需要的,那些看起来不太值钱的东西其实是特别值钱的。“根据这样的动机,商业关心的是心灵的弱点,而不是心灵的优越性,因为只有弱点才能够被利用”。为说服大众,为迎合大多数人,商业试图构造并推广一种以平庸为最好价值的社会普遍观念。(参见[4])。平庸观念不仅克服了曲高和寡的传播难题,同时戏剧性给赋予人们“高贵”的幻觉(与时尚类似)。卡尔·克劳斯在批评煽动家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煽动家的秘诀就是表现得像他的听众一样愚蠢,好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像他一样聪明,商业的“平庸”策略对人们的煽动正是利用了大众的这种心理弱点,它以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将心灵平庸化,进而将人商品化。在物质的诱惑和商业策略的迷惑下,人们常常忘却自己的真正需求,盲目地奔走于无尽的消费链中,以一种癫狂的状态把“自我”及生活意义消费掉了。
……
楚门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但楚门本身却并不假,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我们本身却可能不“真”。现代性(modernity)强调自我,而讽刺的是,现代人无限扩张自我之时,却反而丧失了“真”的自我。现代人对自我的丧失不仅不是因为放弃了自我,而恰恰是把“自我”过分观念化、规范化、商品化、平庸化,这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如何反思当下的生活状况,如何走出现代文明所构造的迷梦,我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当代问题。
“早上好,顺便预祝午安和晚安。”楚门带着标志性的笑容离开了剧场。不过,当楚门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他会后悔吗?这里依然充斥着虚伪、谎言和人性的罪恶,这里依然不能让我们自信地回答“我是谁”,这里依然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是其所是地生活,这里依然不能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开拓生活的意义。但我相信,在虚构的生活和充斥着虚假的真实生活之间,他仍然会选择后者,因为后者即便很糟糕,它仍有改变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无论是否喜欢这个世界,我们都不能像楚门一样潇洒地离开,我们只能选择改变,改变自己,改变世界。或许,我们所需做的是,追随内心最本真的渴求,拥抱世界,创作一个使心灵得以卓越的真实生活。
有个微博段子很是可爱:“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穷人都能看得起病,百姓住每月77 元的廉租房,工资增长11%,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9%。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物价不涨,道路不堵,环境改善,犯罪伏法。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将我埋葬在新闻联播里。”
如果某天楚门也在织微博,也看了这个段子,我想,他也许会这样回复:“你好,世界。你虽丑陋,但很迷人,因为我相信,你终究会变得美丽。如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我愿让尸骨散落大地,因为我喜欢这个世界的真实。请不要把我埋葬在‘新闻联播’⑥里。”
注释:
① 1950年,阿兰·图灵在《心灵》(Mind)杂志发表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计算机器和智能》 。文章认为“机器能不能思考”可等效为“机器能不能通过他设计的图灵测试”,如果机器能通过这个测试,则可以认为此机器具有思维能力。
② 一个关于同一性悖论的著名讨论:如果病了的苏格拉底与康复了的苏格拉底是等同的,那么病了的苏格拉底所具有的每一个特征就被康复了的苏格拉底所具有。但那样的话,健康的苏格拉底仍然是病了的。
③ 牛顿经典理论描述了一个机械的、决定论的世界图景,拉普拉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妖。据说拿破仑看了拉普拉斯的著作后,疑惑地问拉普拉斯为何他的书中从未提及上帝,拉普拉斯回答说,在他的理论体系里,不需要上帝。
④ 在康德之前,知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知识是否和客观事实吻合,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主体都在围绕客体转。然而,经验主义常常导向怀疑主义,而理性主义则不得不面对着无穷论证。康德为克服主客二元在认识论上的难题,创造性地让客体绕着主体转,这一转变,康德自诩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对此,赵汀阳有个有意思的评论:“哥白尼纠正了一个错觉,而康德却制造了一个错觉,使人们误以为世界以人为中心。”
⑤ 维特根斯坦曾把哲学比喻为在瓶子里找不到出路的苍蝇,在瓶子里乱飞。
⑥ 一种新闻节目形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网民常将新闻联播隐喻为:一种不真实的美好。
参考文献及推荐阅读:
[1] 索伦森:悖论简史。
[2]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
[3] 赵汀阳:论可能生活。
[4] 赵汀阳:千年观念故事。
[5] 赵汀阳:作为产品和作为方法的个人。
[6]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
[7]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本文遵循CC知识共享协议(署名/非商业用途/禁止演绎)。
本文授权「微思客」发表于wethinker.com,特致谢「微思客」对本文的推送。